
全國24小時熱線
400-660-18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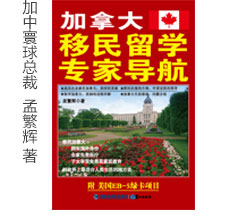
巴黎郊外的小村莊奧維,因為畫家梵高死在這里而聞名,他自殺的那間小客棧的房子至今還保持著原貌。他活了37歲,那間房子是他一生中住過的第38間房子,在他死之后就沒人再居住過。墻壁上有“梵高之友”的一個告示,上面說,如果大家捐款給“梵高之友”協會,那我們就可以在這里掛上一張梵高的真跡。
畫家和他的弟弟就葬在村外的公墓里,墓碑前是一叢綠色的植物。小村子周圍有幾十個“景點”,都是梵高寫生的地方,樹立著他的畫作,你可以把眼前所見與畫家筆下的景色相對照。最著名的一處就是“奧維的教堂”。
這幅畫的真跡在奧塞博物館,塞納河邊一座老火車站改建的美術館,梵高畫作的那個展室總顯得比別的展室擁擠一些。
是的,梵高并不是法國人。一個美國人寫的傳記《渴望生活》讓我們首先認識了這個畫家,也將法國認同于藝術之國。畢加索不是法國人,莫迪里阿尼也不是法國人,但今天只在法國,你才有機會看到新近拍攝的有關莫迪里阿尼的電影。如同美國人認為他們對全世界的安全、民主與自由負有一種責任相類似,法國認為他們對全世界的文化負有責任。
1519年,當達•芬奇老死在今日法國盧瓦河邊的安布瓦斯城的時候,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說,達•芬奇死在了他的懷中。而這位國王是一個美術愛好者兼藝術伯樂,文藝復興的諸多作品都因為這位伯樂,而留在了今日的法國境內。
還記得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嗎?卡西莫多讓我們看到了在中世紀之后人性的普遍覺醒是多么的艱難,這恰恰是文藝復興時代法蘭西給我們留下的最大的遺產。當法國最偉大的抒情詩人維永被扔進蘇盧瓦地牢五個月后,作為第一個活著出來的人,他用文字記錄了一切,這等同于有人從地獄跑了出來,然后寫了本地獄游記。文字的力量幾乎成為了法國近代影響力的基石,從伏爾泰到巴爾扎克,盡管法語在今日世界只覆蓋了北美的魁北克省和北非的部分地區,但是法語文字的思想能量,早已經超越了文字的富含。
長久以來,法國的大腦也是世界思想界活躍的力量,孟德斯鳩、盧梭、羅蘭•巴特、笛卡兒,我們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字。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被路易十五查禁,狄德羅被關了三個月,但這并不影響這些思想最終出爐。也許現在追溯18世紀的啟蒙運動和百科全書派已顯得有些迂腐,我們更喜歡波伏瓦那樣的人,她的書《第二性》影響了許許多多男人和女人,但有更多的人是因為她的人生故事才懂得她的人生哲學。“法國思想家”這個詞匯,在近50年來可以有另一種表達方式,那就是法國文化偶像。
加繆的《西西弗神話》通俗易懂,開篇就說:真正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判斷生命值得不值得經過,這就是最大的哲學問題。這本小冊子是60年代法國學生和80年代中國學生的枕邊書。1998年的時候,法國許多雜志都在回顧30前的那場運動,《巴黎競賽畫報》說,那場運動要改變的是生活方式而不是政府;《新觀察家》說,那是一場“改變了一切的虛假革命”。
思想上的革命總是虛假的,但它確實發生了。1985年薩特去世的時候,存在主義正在中國的大地上開始新一輪啟蒙。
羅伯•格里耶的小說,在中國的印數比在法國的印數要多,他知道這個情況后調侃地說:“這證明中國人比法國人還有文化。”是的,我們是有文化,我們了解法國的歷史,法國這個概念,如果上溯到巴黎主教圣丹尼被砍頭的261年,那還不如稱之為巴黎時代,那時候巴黎就是法國的種子和核心,法蘭西民族和法國這個概念至少要1000年以后才會浮出水面。但這并不會消磨今日法國的輪廓,就如同塞納河上的西岱島不能淹沒一樣,巴黎圣母院早在1163年就在這個小島上拋下了第一塊基石。我們也知道法國大革命,在這次革命前的450年,英法戰爭中被英國掠去的太子查理,直接造成了三級會議,也就是民眾參政的機會,這種循序漸進的民主與法制,恰恰是文明現代化的推動器。人民不再需要圣女貞德,也不再需要拿破侖。法蘭西人在國家內憂外患的時候同仇敵愾,在國家安定祥和時卻不安于現狀,這種特性被法國知識分子稱為“托克維爾規律”,那是第一共和國到第五共和國的動力。我們知道馬賽曲,我們知道1791年的《人權宣言》,我們還知道“拿破侖法典”,我們知道巴黎公社和《國際歌》,我們知道戈達爾,呂克•貝松,知道法國人的度假與罷工,知道路易•威登和Chanel No.5,LANCEL和嬌韻詩……
法國作為一個明確的文化符號,直接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共享的語言空間。我們將一個國家和一種文化簡單化之后,更容易理解它,“法國是自由和浪漫的”,人民能夠自由的交流和表達,是一個國家創造力的來源,這種創造力不僅體現在科技的進步與藝術的豐富之上,也滲透在生活方式之中。哪怕是在一瓶香水之中,你也能窺見法國的價值。
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