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24小時熱線
400-660-18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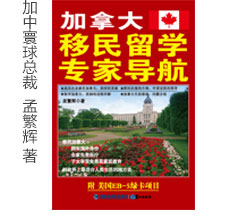
坐落在圣日爾曼大街172號的“花神”咖啡館(Cafe de Flore)和170號的“雙叟”咖啡館(Les Deux Magots)是巴黎頗負盛名的兩家咖啡館,都有100多年的歷史,也都是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因為著名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光顧而聲名鵲起。
現在,這兩家咖啡館表面上都是人滿為患,但要讓某個巴黎知識分子選一個咖啡館坐下來,那就只有一個選擇——“花神”,仿佛是一種神秘的不可打破的操守,即使前者滿座也不可以“雙叟”取而代之,細問之下,卻只會引來尷尬,很少有人能說出個所以然來。
說起來挺難讓人理解的,兩家咖啡館相聚不過十幾米,中間僅隔著一條狹窄的街巷,里里外外沒什么差別太大的地方,可在巴黎的風氣中,“花神”是一如既往地時髦,而“雙叟”卻不怎么入流了,生意雖不錯,不過都是慕名而來的游客。
想當年,“雙叟”咖啡館卻也有一段風光的歷史。店名源自不知道哪個年代掛在墻上的兩個中國清朝官員的木雕,在王爾德光顧之前,它們就在哪兒了。喬伊斯總是和朋友在此暢飲瑞士白葡萄酒,如果碰到海明威就破例陪他喝杯雪莉酒;在三四十年代,加繆、薩特和波伏瓦圍坐于此探討存在主義。就是在“雙叟”,薩特注意到那位“哲學主義的侍者”:“他的動作迅速而魯莽,朝顧客走過去,還沒到跟前,就微微欠了下腰,眼神已經流露出盼望他們趕緊點完的急躁來”。
可這一切都成了過去時。巴黎感動過世界各地的文學青年,除了巴黎人自己,他們對這個城市的生活安之若素,并不會為了懷舊而偏愛哪家咖啡館。歷史已經像灰塵一樣,從咖啡桌上抹去,關鍵是要坐在“正確”的地方,盡管不耐煩的侍者并不是“雙叟”的特產。總得有什么原因,讓某些重要人物只選擇在“花神”落座,并讓更多的人為了顯得像一個地道的巴黎人而追隨。在探究之前,還是先來了解一下法國人的思維習慣。
對于任何一件事,從法國人那里,你能得到三個順序有秩的解釋:人為因素、意識形態上的原因,又或者沒什么可解釋的。你買的電視機壞了,打電話叫人來修,你得到的第一個回答一定是修理工不知道哪兒去了(某個人的原因);一個星期之內不可能處理完,店里有規定(意識形態);很正常啊,沒聽說過哪臺電視不會壞的(還用解釋么)。同樣的思路也適用于法國大革命:都是伏爾泰鬧的(這個不負責任的修理工);馬克思說了資產階級和貴族的斗爭是必然要發生的(店里的規定);福柯:沒什么好說的,西方文明的發展都是恐怖統治的結果(是電視機都會壞的)。
說到兩個咖啡館的興衰,兩個關鍵人物不得不提。一個是“花神”的老板布巴爾,另一個卻不是“雙叟”的老板,而是對街里普小酒館的老板卡茲。“里普”也是圣日爾曼大街上一個很有人氣的去處,它供應的阿爾薩斯風味飲食在法國的政客和時尚人物之間頗為流行。布巴爾和卡茲從同一個省來到巴黎,算是老鄉,雖然心下都有點瞧不上對方的事業,倒也和和氣氣,處得像一家人似的,是指那種真正意義上的一家人——彼此依賴、猜疑、厭惡。在50年代,他們的關系很緊密,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個聯盟。而“雙叟”老板性格相對孤僻,游離于這個聯盟之外,漸漸就和他的咖啡館一起被孤立了。
另一種比較意識形態的說法,要回溯到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花神”那時候是右翼分子莫拉斯的地盤,因為他的頻繁光顧,“花神”被戴上了右翼咖啡館的帽子,“雙叟”于是在一種被動的狀態下成了左翼的陣營。莫拉斯對法國文學流派產生過重要影響,同時他也是帝制復辟的倡導者和激烈的反猶分子,為了避開他,薩特和波伏瓦經常在“雙叟”聚會,卻逐漸引來很多游客只為看他們而占滿了咖啡館里的座位,此時“花神”二樓隱蔽的空間顯得格外吸引人,眼不見誰為凈呢?老邁的莫拉斯來“花神”的次數越來越少了,左翼知識分子們權衡了一下,頭也不回地去了“花神”,這才有了后來“花神”是存在主義者據點的說法。
當然也有第三種解釋。按照索緒爾的理論“黑色所以為黑,是因為有白色”,那“花神”之所以時髦,是因為“雙叟”在那兒。時髦的存在需要不時髦作參照,當下這個時代,“雙叟”就成了那個不幸的參照物,其實對“花神”和“雙叟”誰土誰時髦的判斷難免武斷,可在一個時尚之都,武斷是它必不可少的一種品質。人總是有選擇的欲望。即使面對兩個姑娘,一樣美麗,一樣善良,有人也要分出孰優孰劣,這個人的名字就叫巴黎,這時候非得有那種自以為是的勁頭才是。
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