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24小時熱線
400-660-18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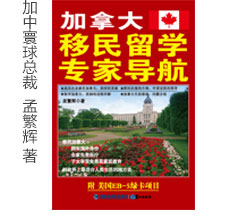
法語的知識分子一詞“Intellectuel”,在口語中被拼成“intello”,歷來包含貶義和侮辱。如果沒有百年前的德雷福斯案件,很可能就不會有上升為精神榮耀和社會良知的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概念。
1894年,法國陸軍部情報處在排猶情緒的驅使下,證據不足仍濫用職權,以莫須有的間諜罪和叛國罪將見習參謀、猶太軍官德雷福斯逮捕,刑訊威逼他承認向德國出賣了情報,最后通過秘密審判判處他無期徒刑并開除軍籍。一年半后,曾經參與案件審判的軍官皮卡爾在非常偶然的情況下發現真正的間諜另有其人,于是向軍方提出重審案件,但軍方和政府都出于維護面子的心理斷然拒絕,并刻意掩蓋真相,將皮卡爾調職發配。消息傳出后,一些有良心的記者、作家覺得無法容忍這種對正義和法律的公開踐踏,開始了營救德雷福斯的努力。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報》上發表致共和國總統的公開信,主編克雷孟梭將標題改成后來在歷史上振聾發聵的三個字“我控訴!”左拉對軍方“侵犯人權,褻瀆法律”的猛烈抨擊,激勵無數被蒙蔽的法國人加入到挽救法蘭西良心的行列,也使他自己遭到了軍方的審判,被迫流亡英國。德雷福斯案件演變成全國性的政治事件,以自由知識分子為代表的重申派不屈不撓,經過八年的反復抗爭,終于使德雷福斯案件得到重審,最高法院在1906年7月判決德雷福斯無罪并恢復軍職。
在德雷福斯案件發生之前,“知識分子”這個詞從來沒有作為特定含義出現過,直到左拉發表《我控訴!》,克雷孟梭才在隨后的社論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這個詞,以此來代表正義的陣營。1991年,法國“新哲學”領袖雷威(Bernard-Henri Levy)以著作《自由的冒險歷程》為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立傳,書中他重新闡述了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知識分子”作為對20世紀歷史最有影響力的概念,其要素如何一步步顯現:第一,左拉那樣的行動,就像他在《我控訴!》中所寫的,“以全人類的名義看到光明”,以犧牲自己的聲譽、財富、安寧為代價去說出追求正義的渴望。雷威將這種行動定義為對知識分子概念的唯名論回答。第二,相當的數目。知識分子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左拉并非單槍匹馬,他的背后有著名的共和黨人克雷孟梭、社會民主黨人饒勒斯,有著名作家法朗士、普魯斯特、紀德,還有許許多多不可能被歷史記載的無名的普通人。第三,某種明確而相對穩定的價值觀,不被強權左右的對正義和良知的認定。
從某種意義上,法國20世紀知識分子的思想史在80年代戛然而止。薩特、福柯、羅蘭•巴特、布羅代爾這些大師在這十來年的相繼去世,使得他們身后驟現空白。如果要概述這一代法國知識分子身上的主體精神氣質,可以說一半是自由和冒險,一半是思想和“介入”。承繼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的盧梭式使命,法國知識分子總想為整個人類設計出一種宏偉的理想藍圖,也就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構理性”——崇尚浪漫理想,偏重于激情和愿望,凸顯知識分子的社會價值。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戰,20世紀的歷次戰爭和重大政治事件都是法國知識分子的活動舞臺:西班牙內戰,抵抗運動,阿爾及利亞戰爭,1968年的紅色五月……雷威在《自由的冒險歷程》一書中用濃墨重彩來記述的作家馬爾羅可以充當最完整的樣本。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馬爾羅以反戰反法西斯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發起募捐,用二十幾架飛機組成一支“馬爾羅國際志愿空軍中隊”。他晚上在旅館里和海明威、聶魯達等人高談闊論,白天親自率領隊員執行轟炸任務,幾個月后飛行隊傷亡慘重,他自己也兩次負傷。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經歷了參軍—被俘—越獄—消極—抵抗,最后成為游擊隊里的傳奇人物,1944年出任兩千多人的阿爾薩斯•洛林旅指揮官,是法國北部地區解放的功臣。作家加繆同樣也是知識分子抵抗運動的代表人物,他一直參與《戰斗報》的編輯工作,戰后卻拒絕法國政府頒發的獎章,因為他覺得死去的人和這樣的榮譽更為相稱。馬爾羅的后半生追隨戴高樂,在政壇結束了他以知識分子身份所擔當的使命,薩特、加繆、阿拉貢則繼續他們作為知識分子的“介入”,只要他們發表聲明,整個世界都會向法國轉過頭來。
甘愿為自由而冒險,充當正義和政權的中介,這是法國知識分子為自己劃定的歷史角色,雖然難免一廂情愿,左右搖擺,但畢竟“這就是我的立場”。
來源:網絡